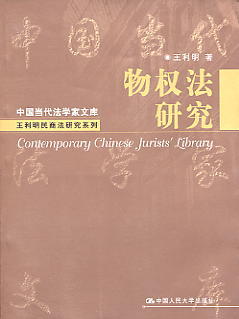
《物權(quán)法研究》
第八節(jié) 物權(quán)法的內(nèi)容和體系
一、物權(quán)法的重心是規(guī)范不動產(chǎn)
在民法上歷來存在著動產(chǎn)與不動產(chǎn)的區(qū)分,這一區(qū)分最早起源于羅馬法。大陸法系國家都采納了這種區(qū)分。如《法國民法典》第516條規(guī)定:“一切財產(chǎn),無論是有體物還是權(quán)利,都可以分為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。”法國民法按照財產(chǎn)的性質(zhì)用途以及是否附著于不動產(chǎn)等多種標準對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做出了區(qū)分。而德國和其他國家沒有像法國民法那樣對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做出了細致的區(qū)分,但一般認為土地及其定著物為不動產(chǎn),其余為動產(chǎn)。①在普通法國家,也采納了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的區(qū)分方法。“英國法將財產(chǎn)區(qū)分為不動產(chǎn)和動產(chǎn)。前者是指不包括租賃保有地的土地上的權(quán)益;后者是指可移動的財產(chǎn)以及租賃保有地。不動產(chǎn)通常稱為realty,動產(chǎn)通常稱為personalty或chattels。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租賃保有地通常被稱為 chattelreal(屬物動產(chǎn)或準不動產(chǎn)),而所有其他動產(chǎn)則被稱為chattel personal (屬人動產(chǎn))。”②土地及其附著物相關(guān)的各種利益(包括法定地產(chǎn)權(quán)、衡平利益、定期利益、地役權(quán)以及對于地契、土地附著物、池魚乃至房門鑰匙所有權(quán)等),均屬不動產(chǎn),其余則為動產(chǎn)。①在我國,根據(jù)《擔(dān)保法》的規(guī)定,所謂動產(chǎn)是指不動產(chǎn)以外的物(第92條第2款)。根據(jù)《擔(dān)保法》第92條“本法所稱不動產(chǎn)是指土地以及房屋、林木等地上定著物”,因此,在我國法律上的不動產(chǎn)范圍以《擔(dān)保法》第92條的規(guī)定為準,即不動產(chǎn)包括:土地、房屋和林木等地上定著物。
從物權(quán)法的發(fā)展趨勢來看,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呈現(xiàn)出相互滲透甚至是相互轉(zhuǎn)化的狀況,因為一方面,由于不動產(chǎn)證券化趨勢的發(fā)展,不動產(chǎn)具有動產(chǎn)化的趨向。物權(quán)的證券化不僅有利于充分實現(xiàn)不動產(chǎn)的交換價值,也為物權(quán)人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。另一方面,某些動產(chǎn)如船舶航空器等也要在法律上采取登記制度,從而與不動產(chǎn)的規(guī)則完全一致。還要看到,在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中,不動產(chǎn)抵押和動產(chǎn)抵押基本上是采用相同的規(guī)則。正是由于這一原因,也有一些學(xué)者認為應(yīng)當(dāng)使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規(guī)則統(tǒng)一化。
我認為,在物權(quán)立法過程中必須注意到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在某些方面應(yīng)適用共同的規(guī)則,例如物權(quán)法的基本原則、物權(quán)的請求權(quán)制度等對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都是適用的。但也要看到,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主要適用的仍然是兩種不同的規(guī)則,具體表現(xiàn)在,第一,從權(quán)利的取得方式來看,動產(chǎn)取得的一些方式如先占、添附、加工、拾得遺失物、發(fā)現(xiàn)埋藏物、添附等,一般不適用于不動產(chǎn)。第二,從權(quán)利的轉(zhuǎn)讓來看,動產(chǎn)的轉(zhuǎn)讓不僅可以采用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,還可以采用其他形式。法律對于動產(chǎn)的轉(zhuǎn)讓合同,常常沒有嚴格的形式要件要求,但對于不動產(chǎn)則具有這方面的要求,不動產(chǎn)交易需要作成書面合同。尤其是在不動產(chǎn)之上設(shè)定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以及轉(zhuǎn)讓土地使用權(quán)和房屋所有權(quán)的合同,都需要經(jīng)過登記。而登記的基礎(chǔ)是當(dāng)事人達成的書面合同,有關(guān)這些合同生效的要件、不動產(chǎn)權(quán)利移轉(zhuǎn)的條件等,法律需要規(guī)定。①第三,從公示方法來看,動產(chǎn)所有權(quán)移轉(zhuǎn)以交付為要件,而不動產(chǎn)所有權(quán)移轉(zhuǎn)以登記為要件。由于登記較之于交付更為復(fù)雜,所以物權(quán)法應(yīng)當(dāng)對登記的程序等做出規(guī)定,這些規(guī)則一般不適用于動產(chǎn)。第四,在他物權(quán)的設(shè)定方面,動產(chǎn)一般不能夠設(shè)定用益物權(quán),只是在法律明確規(guī)定的情況下可以設(shè)立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,如動產(chǎn)抵押、動產(chǎn)質(zhì)押和留置權(quán)。一般來說,在動產(chǎn)之上設(shè)立的他物權(quán)是有限的,而在不動產(chǎn)之上則可以設(shè)立多項物權(quán),各項用益物權(quán)基本上都是在不動產(chǎn)的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的。第五,在權(quán)利的性質(zhì)方面,法律對動產(chǎn)的移轉(zhuǎn)和取得極少設(shè)定一些限定,但是對不動產(chǎn)的設(shè)定、取得、移轉(zhuǎn)常常有許多公法上的限制。第六,動產(chǎn)在交易過程中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規(guī)則,但就不動產(chǎn)而言,如果發(fā)生登記的錯誤,第三人信賴登記而與登記記載的權(quán)利人發(fā)生交易,根據(jù)公信原則該項交易應(yīng)當(dāng)受到保護。
在物權(quán)法中,需要對動產(chǎn)不動產(chǎn)的規(guī)則分別做出規(guī)定,有如下意見值得探討:
1.盡管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動產(chǎn)的價值未必比不動產(chǎn)的價值低,但從物權(quán)法的內(nèi)容來看,主要還是應(yīng)當(dāng)規(guī)定不動產(chǎn)的規(guī)則,在設(shè)置有關(guān)動產(chǎn)與不動產(chǎn)的規(guī)則方面,我國物權(quán)法應(yīng)當(dāng)將重心放在不動產(chǎn)的規(guī)則方面,對動產(chǎn)的規(guī)定主要規(guī)范動產(chǎn)所有權(quán)的取得各種方式,至于動產(chǎn)在交易中的規(guī)則主要適用合同法的規(guī)定。而物權(quán)法中確立的不動產(chǎn)規(guī)則主要應(yīng)當(dāng)包括:不動產(chǎn)的范圍、不動產(chǎn)的取得方式和公示方式、不動產(chǎn)的相鄰關(guān)系和建筑物區(qū)分所有關(guān)系等。
2.是否可以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概括所有的物權(quán)的標的,而不必在物權(quán)法中單獨規(guī)定物權(quán)標的的規(guī)則?我認為,物權(quán)法不能僅僅通過規(guī)定動產(chǎn)與不動產(chǎn)的概念概括所有物權(quán)的標的。誠然,國外有一種立法模式是僅規(guī)定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,概括各種特殊的物權(quán)標的,對各種特殊類型的物,推定其為動產(chǎn)。如(魁北克民法典)第907條規(guī)定:“所有的其他財產(chǎn),如果未被法律規(guī)定,視為動產(chǎn)。”我認為我國物權(quán)法中不應(yīng)當(dāng)采納這種模式,而應(yīng)當(dāng)在物權(quán)法中詳細規(guī)定物權(quán)標的。
二、物權(quán)與無體財產(chǎn)權(quán)
在物權(quán)法起草過程中,許多學(xué)者認為傳統(tǒng)民法僅僅以有體物作為規(guī)范對象的模式已經(jīng)越來越不適應(yīng)日益變化發(fā)展的社會形勢的需要,當(dāng)今世界正處于知識經(jīng)濟的時代,財富的概念已經(jīng)發(fā)生本質(zhì)的變化,財產(chǎn)已經(jīng)不再是僅僅局限于有體物,而更主要表現(xiàn)為無形財產(chǎn)。我國物權(quán)法不能確認和調(diào)整無形財產(chǎn),那么它就不能夠適應(yīng)社會現(xiàn)實的需要,而且不利于保障和促進知識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。這樣的物權(quán)法在內(nèi)容上也不是反映21世紀的社會變化和需要的法律。我認為這一觀點不無道理,但是值得商榷的。從法律上來說,我認為物權(quán)法主要還是調(diào)整因有體物設(shè)立和變動所發(fā)生的各種關(guān)系,而不應(yīng)當(dāng)確定和保障所有的無形財產(chǎn)。其原因在于無形財產(chǎn)的概念本身在法律上是不確定的。
關(guān)于無形財產(chǎn),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觀點。一種觀點認為無形財產(chǎn)是指不具備一定的形狀但占有一定的空間或能夠為人們所支配的物,如電、熱、聲、光以及空間等在物理上表現(xiàn)為無形狀態(tài)的物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為人們所支配。第二種觀點認為,無形財產(chǎn)是指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。因為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是基于智力創(chuàng)作成果所取得的權(quán)利,它并不是對有體物所享有的權(quán)利,所以常常被稱為無形物或無形財產(chǎn)。第三種觀點認為,無形財產(chǎn)是指除對有體物的權(quán)利以外的其他權(quán)利和利益,如對股票、票據(jù)、債券等的權(quán)利,都可以被稱為無形財產(chǎn),其實質(zhì)內(nèi)容是法律所保護的權(quán)利主體的利益。①我贊成第三種觀點,因為在前兩種觀點中無形財產(chǎn)的范圍都比較狹窄,不能包括無形財產(chǎn)的各種類型,當(dāng)然,無形財產(chǎn)不應(yīng)當(dāng)都受到物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,根據(jù)在于:
第一,對于電、熱、聲、光以及空間等在物理上表現(xiàn)為無形狀態(tài)的物,一般都認為是有體財產(chǎn)的延伸,仍然屬于有體物的范疇,因為它盡管是以一種無形的狀態(tài)表現(xiàn)的,但它仍然是一種不依賴人們客觀意志的存在,而且能夠為人們所支配。所以民法學(xué)者一般認為,在現(xiàn)代物權(quán)法中,有體物是指除權(quán)利以外的一切物質(zhì)實體,即物理上的物,它不僅包括占有一定空間的有形物(各種固體、液體和氣體),還包括電、熱、聲、光等自然力或“能”(energies)。②
第二,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是典型的無形財產(chǎn),也是現(xiàn)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無形財產(chǎn),但不能因為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的重要性,便認為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就是物權(quán),因為一方面知識產(chǎn)品作為一種非物質(zhì)的精神成果,權(quán)利人很難對其進行占有和支配,智力成果也不可能像有體物那樣發(fā)生損耗。另一方面,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已經(jīng)受到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,沒有必要再拿到物權(quán)法中,否則,在物權(quán)法中包括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法,將會使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法不能夠作為獨立的法律而存在,這反而不利于對知識成果的保護,也不利于促進知識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。還要看到,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法的一些基本規(guī)則與物權(quán)法并不完全相同。如著作權(quán)的保護是有期限的,但物權(quán)法對所有權(quán)的保護則是無期限的。當(dāng)然,并不是說物權(quán)法完全不可能作用于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,如以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設(shè)定質(zhì)權(quán),也應(yīng)當(dāng)受物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。
第三,對股票、債券和票據(jù)等的權(quán)利,因為已經(jīng)受到公司法、證券法和票據(jù)法的調(diào)整,因此物權(quán)法不應(yīng)該再調(diào)整這些無形財產(chǎn)。從性質(zhì)上看,這些財產(chǎn)也不應(yīng)當(dāng)受到物權(quán)法調(diào)整,例如,股權(quán)在性質(zhì)上也不僅僅是所有權(quán)的憑證,而且也是一種債權(quán)的憑證,還體現(xiàn)了股東的一種資格和地位,其作為一種混合型的權(quán)利很難受到物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。對債券的權(quán)利主要是債權(quán),也不應(yīng)受到物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。至于票據(jù)等有價證券,也已經(jīng)分別受到票據(jù)法等法律的調(diào)整。各個單行法律分別對各種無形財產(chǎn)權(quán)實行分別的調(diào)整和特殊的保護,不僅可以針對各種特殊的無形財產(chǎn)進行專門化的調(diào)整,而且也避免了傳統(tǒng)民法中對無形財產(chǎn)在法律調(diào)整方面所產(chǎn)生的困惑。當(dāng)然,以這些財產(chǎn)設(shè)定質(zhì)權(quán),也應(yīng)當(dāng)受到物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①。
第四,從物權(quán)法固有的內(nèi)容來看,它主要以調(diào)整有體物為內(nèi)容。因為一方面,所有權(quán)概念完全是建立在有體物的概念之上的。在法律上不可能存在以無體物為客體的所有權(quán),否則將會出現(xiàn)債權(quán)的所有權(quán)、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的所有權(quán)甚至所有權(quán)的所有權(quán),所有權(quán)的概念將會變得混亂不堪。另一方面,在他物權(quán)中,物權(quán)法僅僅只是在例外的情況下以無體物作為權(quán)利的內(nèi)容。例如權(quán)利質(zhì)權(quán)、權(quán)利上的用益物權(quán)等。他物權(quán)基本上是在有體物上產(chǎn)生的,且主要是在不動產(chǎn)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的。還要看到,整個物權(quán)法的規(guī)則都是建立在有體物基礎(chǔ)上的,例如一物一權(quán)、物權(quán)的公示和公信、善意取得等都建立在有體物基礎(chǔ)上的。從根本上說,無形財產(chǎn)之上是很難產(chǎn)生支配性和排他性的,也不可能具有物權(quán)的優(yōu)先性和追及權(quán),所以不能適用物權(quán)法的規(guī)則。
我們說無形財產(chǎn)主要不應(yīng)由物權(quán)法調(diào)整,并非說物權(quán)法完全不能調(diào)整這些財產(chǎn)關(guān)系,從財產(chǎn)的發(fā)展趨勢來看,無形財產(chǎn)將會逐漸發(fā)展,并且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也會越來越重要,而許多新的無形財產(chǎn)未必都會受到各個單行法律的規(guī)范。例如,美國學(xué)者李奇曾經(jīng)在《論新財產(chǎn)》一文中提出特許經(jīng)營權(quán)是一種新的財產(chǎn)權(quán),實際上,特許經(jīng)營權(quán)不完全是一種民事權(quán)利,可能暫時難以得到立法的確認和保護。為了使這些無形財產(chǎn)也可以受到法律的調(diào)整,便需要擴大物權(quán)法適用范圍。據(jù)此我們認為,除法律法規(guī)另有規(guī)定以外,新的無形財產(chǎn)可以準用物權(quán)法關(guān)于物權(quán)的規(guī)定。
三、關(guān)于總則和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
(一)是否要設(shè)立總則
物權(quán)法在內(nèi)容體系上是否應(yīng)當(dāng)設(shè)立總則的規(guī)定,也是確定物權(quán)體系時需要解決的問題。在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中,物權(quán)法部分大都設(shè)有總則的規(guī)定,從而使物權(quán)法更富有體系性。也有的國家的民法典例如《德國民法典》中的物權(quán)法并不設(shè)立總則部分,未設(shè)置的主要原因是對物權(quán)的一般性的規(guī)定在民法典第一編總則中已經(jīng)有一定的規(guī)定,因此物權(quán)部分可以不設(shè)總則。
我認為在考慮是否設(shè)立總則時,必須注意到兩個方面的問題:第一,是否可以在總則中包括物權(quán)法總則的內(nèi)容。應(yīng)當(dāng)看到,民法總則的許多內(nèi)容都可以適用于物權(quán)法,甚至有一些原則主要是適用于物權(quán)法的。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法典的總則已經(jīng)對各種民事權(quán)利的共性問題做出了規(guī)定,便不應(yīng)當(dāng)存在著對各種物權(quán)的一般性的共同規(guī)定。畢竟民法總則是對各種民事權(quán)利共性問題的規(guī)定,而不可能僅僅針對物權(quán)做出一般規(guī)定。尤其是在我國迄今為止并沒有完整的民法總則的規(guī)定,民法總則內(nèi)容主要是在民法通則中規(guī)定的,總的來說,這些規(guī)定仍然十分簡略,并沒有解決物權(quán)法中的共同規(guī)則。例如物權(quán)法迫切需要確認的取得時效制度,在民法通則的訴訟時效中就沒有做出規(guī)定,這就需要在物權(quán)法中專門做出規(guī)
定。第二,是否需要在所有權(quán)中對物權(quán)法的總則問題做出規(guī)定?由于所有權(quán)是物權(quán)中的核心內(nèi)容,他物權(quán)都是在所有權(quán)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的,因此對所有權(quán)的某些規(guī)定也可以適用于他物權(quán)。例如在所有權(quán)中規(guī)定善意取得制度同樣可以適用于他物權(quán)。從我國有關(guān)的物權(quán)立法來看,也曾經(jīng)采納過此種模式。例如在擔(dān)保法中,規(guī)定了對動產(chǎn)質(zhì)權(quán)的一般問題做出規(guī)定,這一規(guī)定同樣適用于權(quán)利質(zhì)權(quán)。因此動產(chǎn)質(zhì)權(quán)的一般規(guī)定可以成為質(zhì)權(quán)的一般規(guī)定。應(yīng)當(dāng)承認,所有權(quán)的某些規(guī)定是可以適用其他物權(quán)的,但完全以所有權(quán)的規(guī)定來代替物權(quán)法總則部分的規(guī)定仍然有缺陷。因為他物權(quán)相對于所有權(quán)的規(guī)定更為復(fù)雜。所有權(quán)的一些規(guī)則只能專門適用于所有權(quán),而不能適用于他物權(quán),例如基于所有權(quán)產(chǎn)生的返還原物請求權(quán)不同于基于他物權(quán)產(chǎn)生的返還原物請求權(quán),因此在法律上還需要單獨設(shè)立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制度,而這種規(guī)定只能在物權(quán)法的總則部分做出規(guī)定。
我認為,總則主要應(yīng)當(dāng)規(guī)定下列內(nèi)容:即物權(quán)法的基本原則、物權(quán)的主體、客體和效力、物權(quán)的保護方法(如物上請求權(quán))、物權(quán)的行使原則等。當(dāng)然,更詳盡、合理的物權(quán)法總則內(nèi)容仍有待于進一步探討。
(二)關(guān)于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
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是指物權(quán)受到侵害時權(quán)利人所享有的一項請求權(quán)。在學(xué)術(shù)上常常采用物上請求權(quán)的概念。物權(quán)的請求權(quán)是一種既不同于債權(quán)也不同于物權(quán)的權(quán)利,而是一種特殊的請求權(quán)類型。誠然,物權(quán)的請求權(quán)是發(fā)生在特定的當(dāng)事人之間的請求關(guān)系,但物權(quán)的請求權(quán)具有不同于債權(quán)的特殊性質(zhì),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本質(zhì)上不同于侵權(quán)行為請求權(quán),不能以侵權(quán)行為的請求權(quán)來代替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,在物權(quán)法中應(yīng)當(dāng)設(shè)立獨立的物權(quán)請求權(quán)制度。
四、應(yīng)當(dāng)區(qū)分用益物權(quán)與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
物權(quán)法的分則體系應(yīng)主要根據(jù)物權(quán)的分類進行構(gòu)建。從大的方面來說,物權(quán)分為所有權(quán)與他物權(quán)。所有權(quán)與他物權(quán)的區(qū)別在于:首先,所有權(quán)是一種完全物權(quán),所有權(quán)人享有對物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處分的權(quán)能,而他物權(quán)人則并不全部享有上述權(quán)能,從這個意義上說,他物權(quán)也被稱為限制物權(quán);其次,所有權(quán)是一種自物權(quán),而他物權(quán)是所有權(quán)權(quán)能分離的結(jié)果,只能在他人的財產(chǎn)所有權(quán)的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;第三,從期限上說,所有權(quán)除非是因為轉(zhuǎn)讓或標的物的毀損滅失,否則在法律上推定其永遠存在,因此所有權(quán)被稱為永恒物權(quán),而他物權(quán)的存在大都有期限上的限制,所以他物權(quán)也被稱為有期物權(quán)。所有權(quán)與他物權(quán)基本上概括了全部物權(quán)的類型,這樣我國物權(quán)法也可以根據(jù)這種分類構(gòu)建其分則部分的體系。在所有權(quán)中主要規(guī)定所有權(quán)的規(guī)則和各類所有權(quán),如國家、集體等主體享有的所有權(quán),在他物權(quán)部分具體規(guī)定各種其他類型的物權(quán)。
就上述對物權(quán)法分則體系的大的劃分,學(xué)者基本都持贊成態(tài)度,但對于他物權(quán)是否有必要進一步做出分類,并在此基礎(chǔ)上構(gòu)建我國物權(quán)法的體系,學(xué)者則存有不同的看法。有的學(xué)者認為,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一般未對他物權(quán)作進一步的分類,加之此種分類也存在困難,因此我國的物權(quán)立法也不需要對他物權(quán)進行分類。我們認為,由于他物權(quán)類型較多,且因擔(dān)保債權(quán)之實現(xiàn)而設(shè)立的物權(quán)與因使用收益而設(shè)立的物權(quán)存在很大的差別,所以應(yīng)對他物權(quán)作進一步分類。我們認為可以將他物權(quán)分為用益物權(quán)與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,換言之,要構(gòu)建現(xiàn)代的、科學(xué)的物權(quán)法體系,應(yīng)當(dāng)在采納用益物權(quán)的基礎(chǔ)上,將物權(quán)法的他物權(quán)劃分為用益物權(quán)和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兩大類。用益物權(quán)是與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相對應(yīng)的,這是根據(jù)權(quán)利人所支配的價值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所進行的區(qū)分。用益物權(quán)人取得的是物的使用價值,物的使用價值的支配性使得用益物權(quán)人對于標的物沒有法律上的處分權(quán),因而用益物權(quán)又可稱之為“使用價值權(quán)”。而作為他物權(quán)另一重要類型的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則側(cè)重于對物的交換價值的支配,它不以對物的實體利用為目的,而是以支配物的交換價值從而確保債權(quán)人債權(quán)的實現(xiàn)為目的。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人所支配的是擔(dān)保物的交換價值,即擔(dān)保物在拍賣、變賣時的價值。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設(shè)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人能夠?qū)?dān)保物的交換價值優(yōu)先受償,以滿足其債權(quán)。用益物權(quán)和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的分類基本上可以將各類物權(quán)做出法律上的劃分。盡管用益物權(quán)和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的分類是傳統(tǒng)的他物權(quán)分類法,但此種方法比較科學(xué)地將各類他物權(quán)進行了劃分,且此種劃分基本上概括了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各種他物權(quán),迄今為止,還沒有更為科學(xué)的方法取而代之。如果沒有這種分類,他物權(quán)體系將是雜亂無章的,因而,這套科學(xué)分類體系理應(yīng)為我國物權(quán)立法所采納。
誠如學(xué)者所言,我國土地公有制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的用益物權(quán)具有一些公有制的特點,例如國有土地使用權(quán)中具有某些政府管理的因素,而承包經(jīng)營權(quán)也不像永佃權(quán)那樣具有強烈的排他性。然而,從本質(zhì)上看土地公有制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的土地使用權(quán)、承包經(jīng)營權(quán)等權(quán)利,與傳統(tǒng)民法的用益物權(quán)一樣都是在土地所有權(quán)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的,是土地所有權(quán)權(quán)能分離的產(chǎn)物,在權(quán)利的內(nèi)容上都包括了使用權(quán)或收益權(quán),這些權(quán)利本質(zhì)上都是私法上的物權(quán),都應(yīng)當(dāng)具有物權(quán)所應(yīng)當(dāng)具有的效力,因此有必要在物權(quán)法中對之加以規(guī)定并定名為用益物權(quán)制度。至于全民所有制企業(yè)經(jīng)營權(quán),雖不能歸入到用益物權(quán)或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中任一種類型,但由于全民所有制企業(yè)現(xiàn)在都改稱為國有企業(yè),而國有企業(yè)是以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為改革的目標模式,企業(yè)是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對包括出資人的出資在內(nèi)的全部財產(chǎn)享有法人所有權(quán),因此,在物權(quán)法的他物權(quán)體系中不必對全民所有制企業(yè)經(jīng)營權(quán)做出規(guī)定,而應(yīng)當(dāng)在所有權(quán)當(dāng)中對企業(yè)法人所有權(quán)做出規(guī)定。在對用益物權(quán)類型做出規(guī)定時,對實踐中出現(xiàn)的各種不違反法律規(guī)定的使用、利用不動產(chǎn)形態(tài)都應(yīng)進行認真的整理和清理,需要物權(quán)法加以規(guī)范的應(yīng)確認為一種用益物權(quán),即使這些權(quán)利在實踐中發(fā)生得很少,也應(yīng)加以規(guī)范,以免發(fā)生糾紛后因缺乏法律依據(jù)而不能有效處理這些糾紛。例如典權(quán),盡管在實踐中很少使用,但隨著公民個人購買商品房日益普遍,出于融資的需要,就有可能采用這種方式。我國物權(quán)法在用益物權(quán)方面,可以主要規(guī)定土地使用權(quán)、農(nóng)村土地承包經(jīng)營權(quán)、宅基地使用權(quán)、地役權(quán)、典權(quán)、空間利用權(quán)等權(quán)利。
五、物權(quán)法應(yīng)當(dāng)規(guī)定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
我國于1995年制定和頒布的《擔(dān)保法》,標志著我國擔(dān)保制度的基本建立,它對于保障債權(quán)的實現(xiàn),促進資金的融通以及市場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近幾年來,隨著我國市場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,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日益復(fù)雜,有關(guān)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的糾紛也大量產(chǎn)生。而擔(dān)保法的規(guī)定對交易當(dāng)事人設(shè)立擔(dān)保確立了基本準則,也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擔(dān)保法的司法解釋提供了法律依據(jù),所以擔(dān)保法的制定和頒布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。由于在擔(dān)保法中規(guī)定了抵押、質(zhì)押、留置三種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,據(jù)此有許多學(xué)者認為鑒于我國擔(dān)保法已經(jīng)對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做出了規(guī)定,所以物權(quán)法沒有必要再重復(fù)擔(dān)保法的規(guī)定,即使擔(dān)保法中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,也可以在將來修改擔(dān)保法時進一步加以完善,物權(quán)法沒有必要涉及這個問題。我認為,物權(quán)法應(yīng)當(dāng)規(guī)定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制度,其原因在于:
第一,從體系上考慮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與用益物權(quán)制度共同構(gòu)成他物權(quán)體系,如果沒有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,則不僅整個物權(quán)法的體系是殘缺破裂的,且物權(quán)法總則的規(guī)定勢必多數(shù)缺乏針對性,成為紙面條款。物權(quán)法作為調(diào)整財產(chǎn)關(guān)系的基本民事法律,必須設(shè)立完整的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制度,因為物權(quán)法中沒有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制度則不能形成完整的物權(quán)法體系,物權(quán)法在內(nèi)容上也就是支離破碎的,而且也不符合其作為基本法的地位。
第二,所有權(quán)制度、用益物權(quán)制度都與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制度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(lián)系,如果不規(guī)定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將會使這些制度難以發(fā)揮應(yīng)有的功能。由于擔(dān)保法中沒有規(guī)定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的概念,因此擔(dān)保法中規(guī)定的抵押、質(zhì)押、留置三種擔(dān)保是否屬于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,物權(quán)法中總則的規(guī)定是否適用于《擔(dān)保法》上的抵押、質(zhì)押、留置制度,等等一系列問題,都是不明確的。
第三,擔(dān)保法本身不是民法典中的獨立部分,擔(dān)保法既包括了人的擔(dān)保(如保證)、物的擔(dān)保(如抵押、質(zhì)押等),還包括了定金。這些內(nèi)容應(yīng)當(dāng)分別由合同法、物權(quán)法加以調(diào)整。人的擔(dān)保屬于合同法的范疇,而物的擔(dān)保屬于物權(quán)法的范疇,擔(dān)保法只是從功能的相似性上將兩者強行結(jié)合在一起,卻并沒有遵循科學(xué)分類立法規(guī)律。如果我們將物權(quán)法和民法典的制定放在一起來考慮,從民法典的體系出發(fā),就應(yīng)當(dāng)將擔(dān)保法的內(nèi)容分別規(guī)定在合同法和物權(quán)法中,將來不可能在民法典之外,還要存在一部獨立的擔(dān)保法,否則,民法典的體系是難以確定的。
第四,擔(dān)保法并沒有完全概括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的各種形式和內(nèi)容,如關(guān)于財團抵押、最高額抵押等制度或沒有規(guī)定,或規(guī)定得過于簡陋。擔(dān)保法的有些內(nèi)容經(jīng)多年的實踐證明也需要修改。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頒布的《關(guān)于適用〈中華人民共和國擔(dān)保法〉若干問題的解釋》,補充了一些擔(dān)保法中未規(guī)定的內(nèi)容,但僅僅依靠司法解釋不能完全解決法律的完善問題,完全等到擔(dān)保法的修改來完善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制度則更不妥當(dāng)。因為擔(dān)保法在制定的時候,社會經(jīng)濟生活中的擔(dān)保現(xiàn)象還不多,許多問題還尚未表現(xiàn)出來,因此,擔(dān)保法中的許多規(guī)定比較簡單,擔(dān)保法制定后出現(xiàn)了一些新的擔(dān)保形式需要加以規(guī)定,司法實踐中處理擔(dān)保糾紛案件的經(jīng)驗也需要總結(jié)完善,這些內(nèi)容需要盡快地通過制定物權(quán)法加以補充、完善。可以說,物權(quán)法的制訂為擔(dān)保物權(quán)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契機。
① 參見《德國民法典》第94條,《日本民法典》第86條,《瑞士民法典》第655條。
② [英]F.H.勞森,B.拉登:《財產(chǎn)法》,18頁,北京,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,1998。
① 參見李雙元主編:《比較民法學(xué)》,251頁,武漢,武漢大學(xué)出版社,1998。
① 至于有關(guān)書面合同的內(nèi)容,是否有必要在物權(quán)法中單獨做出規(guī)定,學(xué)術(shù)界存在爭論。例如,我國擔(dān)保法對抵押合同和質(zhì)押合同的內(nèi)容做出了明確規(guī)定,有人認為這些合同應(yīng)當(dāng)受到物權(quán)法的調(diào)整。
① 參見馬俊駒,梅夏英:《無形財產(chǎn)的理論和立法問題》,載《中國法學(xué)》,200l(2)。
② 參見李雙元主編:《比較民法學(xué)》,247頁。
① 參見馬俊駒,梅夏英:《無形財產(chǎn)的理論和立法問題》,載《中國法學(xué)》,2001(2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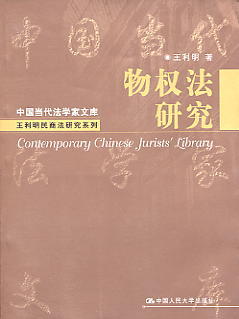 《物權(quán)法研究》
《物權(quán)法研究》